1
今日闲聊,与舍友帅清聊起农村的变化,他突然说:“这几年农村变化太大了,很多东西都消失了。比如炊烟几乎不见了。”记忆中,小时候的乡土农村,做饭都用到柴火,烧起来就有一股股青灰色的炊烟从家家户户的厨房屋顶升起。村里人把这做饭的炊烟叫着烟火,谁家有烟火,证明谁家有人谁家做饭了,谁家没了烟火,谁家就没人了。
时过境迁,做饭正逐渐告别烟熏火燎,生火才可以做饭的技巧不在是一个农村孩子成长的必备技能了,社会的进步,做饭点火只需简单地按下开关键,渐渐很多人就会忘记蓬草、树枝、煤炭做饭时燃烧的味道,几代人以后或许会不明白柴火为何物。慢慢的人们看到“烟火”二字,想到的大概只有天空中因为喜庆而燃放的绚丽色彩了,可能没有人会想到生火做饭的烟熏火燎了。今天我在告诉大家的烟火,就是存在于村落做饭时的烟火,在中国的农村氤氲了几千年的烟火,喂养了中国农村人几千年的柴火饭,是一种记忆,是一种味道,是一种景观。
“想吃柴火饭”是苏泊尔电饭煲打出的广告语,他们或许只想用有关柴火的有关记忆引起自己产品的关注。那么关于柴火的记忆,就从准备柴火说起,那是前些年农村一年生计中主要的生活事项,树枝、秸秆、杂草准在晴天备好晒干,贮藏起来用来做饭。
2
春天是收集树枝的最好时机,农民喜欢在清明前后修剪树木,被修剪掉的树枝则拿回来晾晒一个春天就变成最理想的柴火,农人像小孩子堆砌碉堡般整整齐齐地把这些树枝安置在大门旁或者院落里,经过风吹雨打这些柴火变得干枯易燃。同样是树枝干成的柴火,在奶奶的眼里不同的树枝最后成为的柴火的火力等还是不一样的,奶奶常说杨柳枝易燃,火力一般,适合煮面和烧米汤,槐木火力大最耐烧适合烧油煎油饼,松柏枝条最珍贵仅用来煮肉,用松柏枝条煮出的肉最美味,其他柴火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这些使用柴火的秘诀奶奶把它传给了母亲、大娘、三娘、甚至村里母辈的所有妇女,从每一家柴火的味道就可以大概判断出这家人饭做了什么。这些人把这一秘诀还没有来得及传给下一代人,就用上了煤炭、天然气、电饭锅等。
秋天庄稼收获了,农作物的秸秆先收割完扔在田间地头,等待干冷的风从西北吹来,吹落了叶子,吹枯了田野,吹来了雪花,秸秆和杂草就可以收拾起来,一捆一捆背回家,一车一车拉回家,堆放在屋檐下,码在闲窑洞里,然后一筐一拢变成炊烟,煮熟米饭,熬成美味,温饱一家人的肚子,直到下一个收割的季节来临,秋雨下落了庄稼,下成了天高云淡,新的收成新的秸秆和杂草就会如期收割装载回家。
冬天,树木的枯枝就会在凛冽的寒风中的掉落,树木就一根根甩掉病死的包袱,轻装上阵,好在来年继续生机勃勃。那些掉落的枯枝那是做饭最好不过的柴火,每家每户都在大风天过后去村子背后的树林里收集树枝,一捆捆带回来安放在院落里,这心中的饭才吃的踏实。放羊娃在冬天的田野中穿梭,傍晚回家的时候也要为家里添一捆柴火,只有这样似乎放羊的工作才是最大化的效益。除夕那天,村里人要请财神爷,也是到山神庙周围找一两根柴火带回家放在灶台,接受完香火的祭拜和厨房的五味熏陶,就在正月二十三这天化成一缕青烟,带着一家人顿顿吃饱天天有柴火的最朴实的愿景腾空而起。
3
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用柴火做饭最容易的季节是春夏冬三季了,少雨加之西北风,干燥的气候使得烧火做饭总是很理想,柴火在灶膛里易燃还容易排烟,总之西北风越紧的日子,灶膛里的火就会越旺;秋雨时令,生火做饭是农村家庭主妇最头疼的事了,多雨的秋天烧火做饭最麻烦不过了,找一顿饭的干柴火总是那么不容易,阴天多雨的季候使得柴火潮湿不易燃,放在灶膛里烧总是冒烟不见熊熊的火焰,做一顿饭就像遥遥无期的艰难旅途,家庭主妇们流着被烟熏下来的眼泪就是不见水开汤煎。
每年的腊月和正月正直北方冬天最冷的月份,这也是农活最少的日子,也是吹着干冷西北风地季节,却是厨房最忙的时候,每家每户的厨房这两个月每天灶膛里的火总是烧着,赶做着各种美味,从腊八开始,就准备着过年,准备着将近四十多天的盛宴,厨房的主妇们给家人烧制每天三餐的美味,给亲朋好友准备着一桌桌酒席,给上天神灵准备着一碟碟祭品……都要在这两个月里从简单的面食烧做到复杂的大鱼大肉,从简单的丰衣足食祈祷到幸福安康。
当我突然这一切都是改头换面时,我开始理解乡土,那是一种多么和谐的循环,食物从土地里生产出来,柴火从自然里寻找,做成饭烧过的灰烬回归田野,继续滋养庄稼,自给自足的和谐和美妙。一缕烟一顿饭满是人间最和谐的生活方式,不用担心污染和环保,也不用担心健康和营养,柴火饭消失的时候起,我们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
4
小时候,做饭总是奶奶和妈妈的事,两个人做饭时,总是少不了我这个烧火的。先要用一把干杂草把秸秆烧着,最好的引火柴最好不过小麦秸秆了,每年农历五月多黄土高原的小麦就可以收割了,收割完以后就放在打谷场碾麦子,麦子最后装进屋子里,小麦的秸秆就留在打谷场,整整齐齐的一层一层堆成一个宏伟麦秸垛,从一个麦秸垛就可以读出主人的麦子收成和主人处理家务的能力,每年奶奶对麦秸垛的堆造就像在要求一件艺术品的雕刻,怎样堆防水怎样堆好看怎样堆……后来,每一次从麦秸垛上取小麦秸秆,奶奶都有严格的要求,要取的整整齐齐,不能浪费,在她的眼里一个麦秸垛不仅仅是家里牲畜最主要的饲料也是生活做饭最不可缺的柴火,更是上天的恩赐稍有浪费就是对上天的亵渎。
在灶膛里点燃一把小麦秸秆,丝丝青烟冒出青幽的色彩飘逸着升上了屋顶,长年累月屋顶就呈现出墨黑色证明着日子的天长地久世世代代,宣告着一顿饭的开始,青烟窜进了人们的鼻子刺激了人们的味蕾,对这一顿饭都会表现出迫不及待,我的记忆里做一顿饭很慢就像一年中等待过年,大概是因为饥肠辘辘的缘故吧!
对于灶膛里冒出的第一缕烟,奶奶总是很留心,尤其是农忙时节,她可以从中看到天气将会如何变化,奶奶总是通过一次做饭的生火冒烟告诉家人准确无误的天气预报,至今她的秘诀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她似乎的确告诉我:“这是灶神的音信,小孩子就听不懂了。”总之很神秘,毕竟每次灶膛里冒出的烟火在我的眼里其实都是一样的,不是奶奶眼里或者鼻子里万千风云有目的有预谋的预示。
麦秸烧过,就赶紧向灶膛里填充其他质地柴火,比如玉米秆、树枝……拉着沉重的风箱,便随着风箱哐哐啪啪的声音火苗就在锅底烧起来,火烧到旺时就会呼呼的响,干燥晴朗的日子里火总是在灶膛里烧的很轻松。每次做饭奶奶对火烧的旺与否总是有要求的,烧水煮饭时奶奶对火候总是没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只要火大水烧开的快就可以了;做菜的时间奶奶一会儿要大火一会要小火,我就在灶膛里一会儿多架柴一会儿赶紧灭火,每次这样折腾下来,我的脸上就会抹上黑色的柴火印迹;做饼子时奶奶就要求用秸秆慢慢地烧小火,不用拉动沉重的风箱,慢慢的慢慢的饼子就烧好了,从锅里拿出来冒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奶奶说:“一道好的菜除了调料就是恰到好处的火候了。”在成家以后的日子里学着自己慢慢烧菜,用着相同的食材和调料,做出来的菜总不及妻子的菜,更不敢设想有奶奶或者母亲烧的菜的那种感觉了,那一种在味蕾里扎根很深的感觉不在是简简单单的调料和火候问题了。
奶奶和妈妈做饭的时间,爷爷就躺在炕头抽着旱烟,那一种奇怪的旱烟味道奶奶似乎诅咒了一辈子,直到去年爷爷检查出严重的肺病才停止,但奶奶依旧每顿要给爷爷烧制美味的柴火饭,父亲每次在家人做饭的时间就小憩一会,饭后便是沉重的农活。柴火饭在我的记忆中就这样用一个小时的烟熏火燎把一家人的亲情烧的日渐温馨。
当我们说起柴火饭时,我们会想到一个漫长的烟熏火燎的漫长烹制过程,一家人围着灶台聊着各种各样的农话,在精准掌握火候和烹制过程的蒸煮炸炒焖后,一家人举起筷子,端起粗瓷大碗,把这人间最温情的时刻下咽,把这人世最纯洁的营养吸收,然后支起一个乡村社会的音容相貌。
5
十四岁那年上初中,每周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星期五放学了,从星期天开始就在学校一天一天的熬着,每顿饭几乎是不热不冷的水泡着馒头,星期五晚饭母亲总会准备好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和炒豆角。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的季节每次从学校回到村头,天就快黑了,每次回到村头第一眼总是望一望自家的屋顶,看看有没有炊烟,看到自己的炊烟就像是一次重生,力量和情绪会就会这炊烟会从灶膛里冒上来一样。通过炊烟就会知道母亲做饭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快熟了还是刚刚开始,然后再看看村里的其他人屋顶,看看他们家的炊烟可以判断出谁的母亲出门了,炊烟就像一种景致镌刻在每一个人的记忆里,让人们急着有关柴火的味道,记着有时光的味道,记着有关家的味道,记着有关故乡的味道。炊烟也像一种温暖袅袅游荡在在每一个人的疲倦的心神里,温暖着心灵,温暖着追梦的路。
屋子好久没有人住,就会落满尘土和阴森的气息,只需要做一次饭,把柴火烧上一个小时,柴火味和饭菜的味道混合成的烟火,便会把屋子弥漫的阴冷空气驱散掉,是屋子重新回归到居人的温馨和舒宜。这一种舒宜就是奶奶常说的“屋子有了烟火就活了,没有烟火的屋子和院落就会慢慢死掉”。如今我也渐渐理解为什么屋子没有人居住就会破败的厉害和迅速。烟火也许就是屋子的灵魂和屋子生命的气息,没有了烟火屋子的瓦砾和砖墙因为缺少灵魂渐渐散架,在风雨中坍塌,就像奶奶说的死掉了。
人们无论走到哪里,总会停下来,生火做饭,柴火曾经是沟通饥肠辘辘的身体与尚未熟热食材最灵性的路径,但快速发展的社会和日渐加重的生计压力使我们与柴火饭渐行渐远,当缺少了这一路径,我们的柴火饭的记忆将走向哪里?我们的柴火饭的灵魂将安置在哪里?我们的社会发展正在努力解决好人、食物、自然的关系,我们对食物的理解不只是明码标价的商品,我们开始审视食物背后的和谐与历程,我们或许就可以叫回奶奶说的柴火饭的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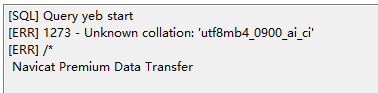






- 最新
- 最热
只看作者